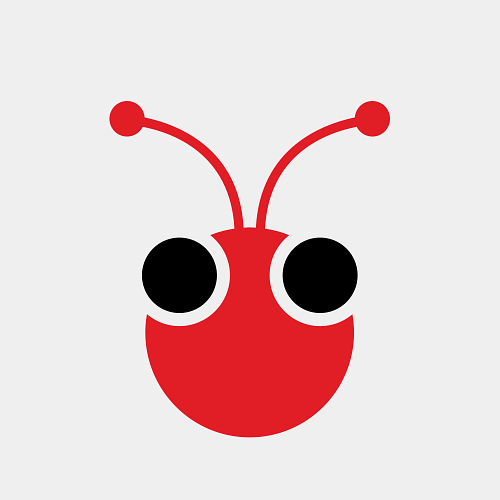最近,乌敏岛附近的海域出现一些旧渔场的棚屋和木板,还有一艘被遗弃的小船。
据《海峡时报》报道,涉事的两家渔场已停业多时。
在附近经营渔场的业者也透露,过去几个月的废弃物越堆越多,相信跟许多渔场撤离东柔佛海峡有关。

新加坡食品局数据显示:
过去两年“关门大吉”的海上渔场有所增加,从2022年的110个减至去年的98个,目前只剩74个。
这些渔场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北部的柔佛海峡。
原本在南部海域经营的两家深海养殖场,因落鳞症暴发导致鱼群大量死亡,已在去年7月终止运作。
临时租用准证费 对小型渔场不是小数目
今年停业的数名海上渔场业者告诉《海峡时报》,食品局曾提供高达10万新元的经济援助配套,减轻他们清盘的财务负担。
一些业者因成本压力加重,难以负荷;有的则因为环境和气候变化,使他们无法达到食品局规定的每年最低产量,即每半公顷海上空间必须生产至少17公吨的鱼。

先说成本。
渔场业者使用海上空间,原本不必付费,只须每年支付更新渔场执照的费用,收费为每半公顷850新元。
不过,从去年起,食品局开始为所有海上渔场提供长期租约。
在这个新的“租约制”下:
渔场业者须支付更高的临时租用准证费,柔佛海峡为每半公顷3600新元,南部海域则是6000新元。
这比之前更新执照的费用高出好几倍。
虽然食品局已豁免去年的临时租用准证费,并承诺在未来四年逐步调高收费,但这对传统的小型渔场来说,仍是相当可观的开支。

在樟宜和林厝港经营海上渔场的The Fish Farmer总裁王典宝直言,撇开临时租用准证费不谈,原本的人手、运输、燃料和鱼饲料等成本也在上涨,导致营运成本急剧上升。
他坦言,渔场业者要申请银行贷款或吸引投资者,向来困难重重,因为银行和投资者一般对水产养殖业缺乏了解,认为这个行业不够稳定,投资风险较高。
从事水产养殖已有15年的Aquablue负责人Joseph Wee,在获得食品局的10万新元经济援助后,也在今年6月关闭渔场。
他花了4万元拆除渔场的建筑结构,其余6万元则存起来当退休储蓄。
Joseph Wee说,维持渔场的建筑结构须投入大量资金,逐年高涨的人力成本也令他吃不消,索性决定退休。
“我原本打算卖掉渔场,将执照转让给买家,但食品局不允许我这么做。”
“我别无选择,不是咬紧牙关继续经营,就是关闭渔场退出市场。”

海上渔场在大自然面前是脆弱的
新加坡的海上渔场业者多数采用传统的开放式养殖法,将鱼养在用渔网制成的鱼笼里。
这种养殖方法的成本较低,但风险较大;渔场设施如发电机、水泵和木板,也容易腐蚀。
有渔场业者受访时说,附近海域的工业活动也会影响水质。
遇到天气热、雨量少的季节,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导致鱼群缺氧死亡,业者就会血本无归。
张富兴在罗央和乌敏岛之间的海道经营“三利海产”已有43年。他在2009年、2014年和2015年曾遭遇三次浮游生物来袭。

张富兴忆述,最严重的一次是在2014年,鱼虾全部死亡,使他亏损了高达30万新元。
“我这一行,可说是看天看海吃饭。自然现象是没办法控制的,我只能从中汲取经验。”
若不幸遇到人为意外,更是雪上加霜。
今年6月,巴西班让码头发生船只相撞事故,其中一艘船的部分燃油泄漏,导致新加坡多处水域出现大片油渍。
尽管食品局第一时间澄清渔场未受油污影响,本地鱼仍可安全食用,但消费者的观感还是难以改变。

陆地渔场经营成本 是海上渔场的四倍
食品局数据显示,新加坡人去年食用的鱼只有8%产自新加坡,其余九成以上都依赖进口。
食品局定下的“30·30愿景”,目标是在2030年以新加坡出产的农产品满足国人三成的营养需求,水产养殖是重要的一环。
不过,随着海上渔场接连停业或缩小规模,新加坡的养鱼业能否扛起这个“重任”,格外引人关注。

学者认为,以目前的传统养殖法,要达到食品局定下的供应量指标,着实不易。
业者必须借助新科技提升效率,例如采用封闭箱养鱼,或发展垂直渔场模式,以降低养殖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
采用封闭箱的做法是:先抽取深海的海水,利用过滤系统和紫外线杀菌,再把干净的海水输送到养殖箱内养鱼。

共和理工学院海洋与水产养殖学系主任陈维龙提醒,新加坡海域出现大量浮游生物的现象可能成为常态。若不改变传统养殖法,难保鱼群死亡事件不会重演。
“在室内打造垂直渔场,将养鱼池‘往上叠’,可以节省土地空间。业者也能改变养鱼周期,赶在淡季前把鱼卖掉。”
虽说高科技养殖法是大势所趋,但所需的昂贵成本未必是小型渔场负担得起的。
Marine Life Aquaculture营运总监陈志文直言,垂直渔场确实可以百分百控制养殖条件,但每年的营运成本至少是海上渔场的四倍。
“经营垂直渔场的前期成本很高,没有30年未必可以抵消。”
“在我看来,垂直渔场至少还要十多年,才可完全取代海上渔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