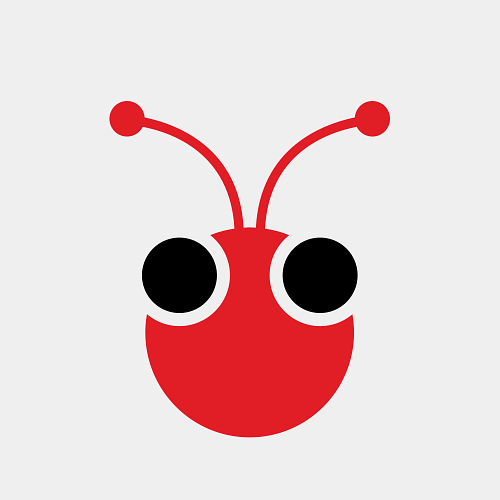上周到香港旅游时,红蚂蚁约了几名香港朋友吃饭。
寒暄了几句,朋友劈头就问:
“香港给你的感觉,跟八年前有什么不同?”
要不是朋友提醒,红蚂蚁还没意识到,上一次访港竟是八年前的事了。
这期间,香港历经了全球范围的冠病疫情,以及疫前被广为报道的“反修例”街头静坐与和平示威,红蚂蚁和其他关注香港的新加坡人一样,边看边捏一把冷汗。
面对朋友的问题,红蚂蚁直言不讳:
“不论走到哪里,耳边传来的都是北方口音的普通话,少了我怀念的‘港味’。”
朋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似乎已料到我会这样回答。

朋友接着说,一项非官方统计显示,香港人口中只剩四成是在香港土生土长、会讲粤语的港人。
看来,过去三年的移民潮影响相当深远。
“今天我们就带你去这四成人口常去的地方!”
来到一家独立书店,店内刚好在举办一场分享会。听着作家与观众用粤语畅所欲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躁动的能量,红蚂蚁这才找回久违的熟悉感。
讲不讲普通话 取决于对方态度?
其实,红蚂蚁的粤语水平只有“半桶水”,都是从小看港剧和港片学来的。
同一首流行歌曲,若有国语和粤语两种版本,也总是觉得粤语版更动听。
此行出发前,红蚂蚁还特地上网“恶补”一番,只为了入境随俗,用有限的粤语词汇与香港的服务人员沟通。
好笑的是,服务人员一听到红蚂蚁的“破粤语”,就知道红蚂蚁不是当地人,反过来用带着“港腔”的普通话安慰道:
“我会讲普通话,你可以用普通话点菜。”

针对《联合早报》香港特派员戴庆成在专栏中提到餐厅限时用餐的“赶客”文化,红蚂蚁并没有亲眼目睹。
反倒是中国大陆食客对餐厅员工“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无礼态度,让红蚂蚁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们可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或目前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
当服务人员用粤语问“想点什么”时,他们眉头一皱,不耐烦地嚷道:
“不会讲普通话吗?”
去年2月就有一名中国大陆网红“沪漂女孩艺轩”,在抖音上载题为《挑战在香港一天只说普通话,会不会被翻白眼》的短视频,“证明”她屡次因只说普通话,遭香港服务人员冷漠对待。

红蚂蚁觉得,这些网红实在没必要“挑衅式”地测试香港餐厅用普通话接待顾客的意愿和能力。
很多服务人员并非刻意歧视,只是处于既无法用普通话流利对话,又无法用英语连贯表达的窘境。
文化语言 VS 政治正确
对许多香港年轻人来说,普通话似乎已成为一种“香港大陆化”的不安提醒,而粤语则象征着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和身份认同。
趁着香港艺术节,红蚂蚁在香港文化中心观赏了新加坡歌手陈洁仪参演的粤语音乐剧《雄狮少年》。
谢幕时,男主角郑君炽用粤语向观众致谢:
“要办一出粤语音乐剧不容易,请大家继续支持粤语音乐剧!”
语毕,不少观众起立鼓掌,红蚂蚁也激动得红了眼眶。

这让红蚂蚁想起“歌神”张学友去年底在香港红馆开唱时,有中国歌迷以普通话高呼:
“能不能多说普通话?我听不懂粤语。”
只见张学友眯着眼,用普通话亲切回应“学一下”,三个字就轻松拆招。
反观性格直率的陈奕迅在澳门面对同样的情况时,却用英语回呛“我喜欢用我想要的方式和语言说话”,踩到不少中国歌迷的敏感神经。
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便开始推行“两文三语”的语文教育政策。
“两文”指的是书面语,即中文和英文;“三语”指的是口头语,即普通话、粤语和英语。
回归翌年,港府就把普通话列入小一和中一的课程,并于2000年把普通话列入中学会考科目。
不过,据红蚂蚁向朋友了解:
香港中小学的普通话课和用粤语教学的中文课是分开教的,而且通常不是由同一名教师授课,因此教学效果不佳。

27年过去了,从香港社会、家庭、校园、广播、影视、办公到柜台服务,粤语依然“一枝独秀”。
近年来北京的对港政策,让粤语在香港的生存空间日益受到威胁,不少港人敢怒不敢言。
香港教育局曾因在网站上列明“粤语是一种中文方言,不是香港的官方语言”而激怒香港民众,最后不得不道歉并删文。
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确实是在中国大陆通商成功与通行便利的关键,这点毋庸置疑。中国官方也坚持要在2025年之前,让普通话的全国普及率达到85%。
但如果说香港人不讲普通话,就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说实在的,就扯得有点远了。
红蚂蚁相信,粤语的生命力极强,绝不会悄无声息地走向式微。
新加坡人回忆里那个“原汁原味”的香港,也不会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洪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