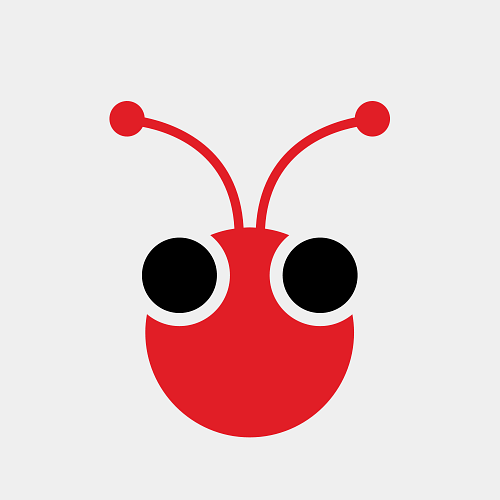说到工作,大部分新加坡人都希望能与生活取得良好平衡,如果遇到要求把时间“奉献”给公司的雇主,一些员工甚至会选择辞职不干,再多钱也免谈。
有趣的是,也曾有数据指新加坡人“上班一条龙”过于拼命,久而久之搞得身体累坏了。
殊不知,新加坡还有一群人的工作模式非常极端:
他们一天打两份工,往往都是在老板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身兼多职”。
疫情期间,当美国经济受到重击时,出现了一个形容有多过一份工作的上班族的用语,这些人被称为“过度就业”(overemployed),并泛指白领员工。
今年1月,新加坡人力部数据曾显示,本地就业人口中在2022年有3.1%以兼职或全职形式从事多项工作。2021年的3.5%则是10年来的新高。
去年9月,人力部长陈诗龙在国会上以书面答复议员询问时则透露,有5万3200名新加坡人从事两份或以上的工作,包括全职及兼职工作,其中约半数从每份工作领取的平均月薪少过1500新元。

因财务压力多打一份工,也有人利用WFH优势
蚁粉可能会心想,自己打一份工作都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这些人怎么会有时间从事第二份工作?
综合本地媒体引述的案例,背后只有一个推动力:为了赚更多钱。
一些人想要有更多钱入袋,不是为了满足什么物质上的需求,而是生活中面对的某些财务压力,情势所逼下才让他们“铤而走险”,在职场上寻找多一条出路。
接受《海峡时报》访问的一名过度就业族X小姐,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30多岁的她是一名教师,每个月领取约3000新元的工资,但自2020年起,她也在一家补习中心担任全职补习老师。
她在家中是唯一能赚钱养家的人,除了要养孩子,也需要另一份全职工作的薪水,来支付父母的医疗及看护人开销。
她说:
“他们每个月的医药费就要好几百元……3000元根本就不足够。”

目前,她的补习老师工作给予她大部分的收入,课程都是在线上进行,一周也需工作五天。
她每天早上6点45分先到学校上课,如果没有负责课外活动,下午2点半就下班。接着,她就继续在线上教补习至晚上9点,之后花一小时陪陪孩子和父母,11点前准时上床睡觉。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员工之所以能兼顾两份工作,也因疫后时代不少企业仍提供灵活工作安排,准许员工继续居家办公。
25岁的G小姐,从2021年开始打两份客服工作,一家公司是网购平台,另一家是电话公司,双双都能远程办公。她这么做,是为了支付大学兼职课程的学费。
“我打算全额付清学费,不想为了上大学而向银行贷款。做两份工作能让我有能力做到,将来考获学位后,也能找到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
虽然新加坡没有相关数据,但据《彭博社》报道,去年一项针对1250名美国员工的调查显示,69%拥有远程或混合工作安排的员工正在从事多项工作。15%的远程工作人士,则至少有两份全职工作。

吊诡的是,加倍付出未必等同于收获更大。
有数据发现,身兼多份工作的美国员工,平均年总收入为5万4000美元(约7万2100新元);反之,只有一份稳定工作者,平均年总收入为6万3000美元(约8万4110新元)。
多打一份工有助于转换跑道?
关键是,在新加坡当“过度就业族”,是否属违法行为?
新加坡没有法律规定员工不能从事第二份工作,多数雇主或人事部,不是被蒙在鼓里、就是难以纠出有哪些员工这么做。
本地疫情暴发不久后,新加坡劳资政公平与良好雇佣联盟(简称TAFEP)曾在2020年5月发表公告说,如果员工的工时受影响,雇主应支持他们从事第二份全职或兼职工作,弥补收入损失,减低冠病疫情对生计的冲击。
2020年9月,碧山——大巴窑集选区议员鍾奇雄也在国会上提出,在遵守“保障员工免于过度劳累、规范潜在利益冲突”的劳工法规下,应允许员工打两份工作,以获取更好的工作保障。
他认为,员工在同一家公司身兼另一个职务,或同时受雇于另一家公司,过程中可学习并应用新的技能。
他补充说,这样一来,员工能培养更广泛的技能,必要时需在短时间内转换职业跑道,也有更大的灵活性。

然而,大部分雇佣合同里都会有明文规定,禁止员工打第二份全职工,如果被抓到可能得面对纪律处分,严重的话会被开除。
也有律师提醒,那些打两份工的员工,应避免任何的利益冲突,比如不应为雇主的竞争对手工作,否则这绝对可作为解雇涉事员工的理由。
除了是否会违反公司利益,选择多打一份工作的员工,最关键的不外是:
要兼顾两份工作的工作量,还得妥善安排时间,在两份工作中多做到尽善尽美,满足两边雇主的要求,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想当左右逢源的“夹心饼”,也必须有“夹心陷”的抗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