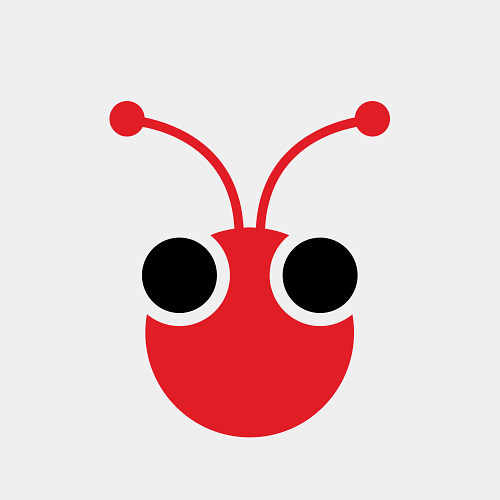除了当年下南洋的老一辈,对于绝大部分的新加坡人来说,应该都不了解年纪轻轻就选择飘洋过海打拼赚钱,只为了给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的那种身负重任的感觉吧。
网络媒体Rice通过访问三名到本地的移民工人(客工)以及他们的家人,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这群帮着建设新加坡的客工们背后的故事、以及他们所思所想。
客工们以英语接受采访,Rice尝试“原汁原味”地呈现客工们的话,红蚂蚁也尝试翻译如下:
28岁的Billal Khan

我的妈妈今年48岁,她曾是一名教师,但现在待在家里照顾我的家人。
我们的感情很好,即使在我离国之前,还在孟加拉的时候,我都会和她分享关于我的一切:我的女朋友、我在外面做的事情,有时她会给我一些建议。
2010年,我来到新加坡,那时我17岁。
这是我的个人决定,我们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耕种、做生意,但我想来新加坡为我的家庭赚更多的钱。
我的爸爸妈妈都不赞同,他们想让我完成学习,所以我偷偷地向培训中心提出了申请。
我妈妈发现后很生气,但是我已经给培训中心付了钱。因此,她一个月没和我说话。
那之后,她说:好吧,你可以去。
她和我一起去机场,一路上哭个不停。我说,我很快就会回来。
那种心情我该怎么解释呢?就是隔着很远的距离,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再见到你爱的人的感觉?
2015年,我趁着开斋节回去给家人一个惊喜。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买了一张去孟加拉的机票。
当天凌晨3点我到家,我告诉妹妹不要出声。
然后,我看到我的爸爸、我的妈妈。那一刻,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通常每天和爸妈通话三次:早上、午餐时和睡觉前。如果我少打一回,我妈妈就会很惶恐。
每一刻,每一秒,我都在想念我的妈妈。
昨天,我得知,也在这里工作的弟弟感染了2019冠状病毒疾病(冠病19)。
我们当然不会告诉爸妈,我们不想让他们担心。我的弟弟还是会打电话给他们,但不用视频通话,这样他们就不会发现了。

Billal的母亲Ruby Akhtar(48岁)
Billal 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他很好,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儿子。每当家里有困难,他都会帮助我们。
当他说他要来新加坡时,我既伤心又担心。他离开家里了很久,我们都很想念他。我怀念每天早上能把他叫醒的日子。我想念他是多么喜欢帮忙做家务。
我总是担心他和他的弟弟。作为一个母亲,我们总是希望孩子和我们一直在一起。
30岁的Mohammed Mukul Hossine

我的妈妈是一名家庭主妇。她60岁了。我非常爱她。她友好、美丽、善良。她和我的爸爸教会我要如何慷慨地、感恩地待人。
我18岁的时候来到新加坡。我妈妈对此很不高兴。当时对我们来说,要说再见很辛苦。
我想念她,想念我的爸爸,我的宠物兔子,我的花园......
头两年,她希望我回家。我们每天都会通电话。她会告诉我,我的兔子是否淘气了,或者花园里开花了。当她看到我对新加坡的生活很满意时,她也就接受了。
2016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Me Migrant”(我,移民)》。我妈妈为我感到无比骄傲。当我告诉她我在写诗时,或者我将关于我的报章报道拍照片发给他们时,她总是显得非常感兴趣。
有时,我会写一些关于我妈妈的诗。起初,我会背诵给她听。我妈妈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她能听得懂。
然后我爸爸说,Mukul,如果你在写关于你妈妈的东西,不要给她看,因为她在心里深深感觉到,但她却永远不会在你面前表现出来。事实上,她哭了,她很想念你,以致于无法正常工作。
我不知道妈妈会这么难过,所以有时我把这些诗放在心里。
我爸爸病了,自2月份以来,我就一直和她及爸爸待在孟加拉的家里。
每天早上,她都会来到我的房间,问我过得怎么样,想吃什么。
我们会去市场购物,她会对我想买的衣服给予评价。这件不错,那件不太好。我喜欢带有印花图案色彩鲜艳的衣服,她也喜欢。但有时她会告诉我,它们看起来像女孩子的衣服。
我们现在每天都在一起,但她知道我想在疫情结束后回到新加坡。
Mukul的母亲Kulsum Bagom(60岁)
当Mukul说他想去新加坡时,我很伤心。我哭得很厉害,根本睡不着。在他离开前,我给他买了很多衣服和水果,比如苹果和橙子。
他离开的第一年最难受。我经常哭也睡不着,因为我实在太想念他了。
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但我还是会担心他。我每天都给他打电话,询问他的工作情况,看看他睡得好不好,吃得好不好?当我做他最喜欢吃的食物时,我很想念他,而他却不在这里和我分享。
当他的书出版时,我非常自豪。我通知了所有的朋友,以及我们村里的每个人。
我很高兴这场疫情把他带回家,我们一家人可以待在一起。可以一起开心,一起悲伤。
47岁的Robina ‘Bhing’ Navato

22岁那年,我来到新加坡,那时我的孩子分别是4岁、2岁和1岁。
我的两个年幼的孩子和我爸妈一起住,而我的大儿子和他父亲住在一起。Airra,排在中间那名孩子,是我唯一的女儿。
我还记得有那么一天,Airra大约1岁半的时候,我甚至还记得她当时穿的衣服,一条紫色的吊带裤,她哭个不停。那天我们没有吃午饭,因为我们没钱。她肚子很饿,直到我嫂子给了她一块饼干,她才停止哭泣。那一刻,我知道我必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来养活我的孩子。
来到新加坡,我既难过又兴奋,同时也为没能陪在孩子们身边而感到内疚,因为我错过了他们的生日和学校的作业项目。
Airra在我离开后6年,才再次见到我。那时她8岁。我化了妆,她看着我,我想她为我感到骄傲吧,就像,哦,原来这是我妈妈。因为她一直以来,都以为我妈妈就是她妈妈。
我觉得她在成长过程中,想和我亲近,这也是我心里所想的,但实际上这很难。
不是我忙于工作,就是她忙于学校或她的朋友,加上假期都很短。但我们的关系在她当上妈妈后改变了。我们走得更近了,当我回去探亲时,我们就睡在同一张床上,孙儿孙女们都睡在我们身旁。有时,她会在我腿上睡午觉。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在一起。
我本来希望她能上大学,但Airra在18、19岁时就怀孕了。
她和我的姐妹们更为亲近,我记得当时她们是最先知道她怀孕的,那时我感到很嫉妒,心想,为什么你知道,我反而不知道?
当她第三次怀孕的时候,她一开始并不想告诉我,因为她知道我会生气。但我告诉她我会永远在她身边,她可以告诉我一切,无论是什么,我都会接受,只是别指望我会感到开心。我告诉她,我当然会生气的,我是你母亲嘛。我想她明白的。
当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他们常常羞于说“我爱你”。但现在他们经常说,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真的很开心。

Bhing的女儿Airra Tejares(27岁)
我妈妈去新加坡工作的时候我才两岁,所以我不太记得那时候的事了。我和弟弟Christopher是由外公外婆带大的。
在我大约8岁的时候,我妈妈回来看我。只有一个星期,所以我们没有多少时间相处,但这是她离开后我第一次见到她。我一直以为她是我的阿姨,直到外婆(丽塔妈妈)告诉我,她就是我妈妈。从那以后,当她不得不回去新加坡时,我会感到难过。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通过电话和信件与母亲保持联系。收到她的消息时会让我开心,但我也很想念她,要求她回到我们身边。每年在我生日那天,家人都会给我买蛋糕和礼物,我也会给妈妈打电话。
她现在每年会回家两次。每次她来的时候,满屋子都是人——孩子们、阿姨们、叔叔们、堂兄弟姐妹们,所有人都到齐。我们的行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我总是在她身边,有她在家我很高兴。
虽然在我生产时,我妈妈无法陪在我身边,但她在2016年1月7日见证了我和先生will的婚礼。她告诉我们必须在那天结婚,这样她才能够出席。我们上午举行了婚礼,她留下吃了午饭,下午就飞回新加坡了。
每次她结束探访飞回新加坡时,我们都不陪她前往机场。我想那是因为她不想让我们看到她哭泣的样子。但是当她回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机场列队迎接她回来。
——————
三名客工、三个家庭、三段故事,装着满满的爱。
红蚂蚁不免想起李显龙总理在4月10日的电视演讲中所说:
“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儿子、父亲和丈夫对新加坡所作出的贡献。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照顾好您的亲人。”
在每一名新加坡“客工”的标签之下,他、她们也是一名儿子、一名女儿、一名父亲、一名母亲、一名丈夫以及一名妻子。让我们时刻牢记这点。
他们在海外打拼即使再辛苦再寂寞再难受,家中永远有深爱着他们的人在等着他们平安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