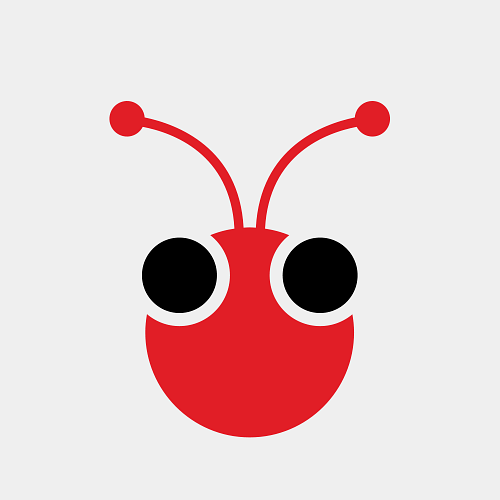“客工”这个词汇,最近在新加坡很常见,也很敏感。
日前有外交官爆出客工宿舍居住条件不达标的情况,过去一周本地的每日新增冠病确诊病患当中,大多数都是外籍客工。客工们人心惶惶,国人也惴惴不安。
今晚(4月15日),新加坡单日新增病例再创新高,达447例,当中有404人都是住在宿舍的客工,累计总病例3699例。
新加坡为阻断病毒传播在4月7日推出阻断措施(Circuit Breaker)后,本地有不少人怨声四起。最能让大众产生共鸣的“烦恼”就是出行不便,商场、景点和娱乐中心都关闭了,周末也不能好好放松出去游玩,感觉人生好痛苦。
而往往发出这种怨言的人,多半都是能舒适地窝在家中,享受“无聊的安全环境”的群体。殊不知,对客工而言,能享有这种平凡的烦恼,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小确幸。
红蚂蚁今天在网上咬到一篇“客工心声”,作者是正在本地客工宿舍里隔离的一名孟加拉客工Md Sharif Uddin(莫谢里夫,音译)。
莫谢里夫在新加坡拥有双重身份。首先,他是一名客工,在新加坡工作了11年。第二,他也是一名得奖作者。2017年出版了一本英文回忆录《Stranger to Myself》(暂且译为:熟悉的陌生人),书中记录了新加坡客工生涯的点点滴滴,相信他是本地第一名出书的客工。

这本书后来荣获2018年新加坡书籍奖(纪实文学类)。那年莫谢里夫39岁。
攸关生存 被恐惧侵袭
莫谢里夫目前就住在其中一个被列为感染群的客工宿舍里。
作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被隔离即代表无法工作,也等同于暂时没有收入。这关乎了远在孟加拉那头家人的存活。莫谢里夫写道:
“我望着开阔的天空。空虚吞噬着我。我的寂寞随着夜里的寂静而加深。我厌倦了人生中的绊倒。现在我在这里、没有工作、没钱——没钱即意味着我的人生的步伐停滞不前。不确定感又来袭,在脑里挥之不去。我只能从日记寻求庇护,将无法言喻的心情起伏写下来。”
“几千名客工们在哭泣,他们正面对一个可悲的生活,被困在宿舍房间里。为了保护我们出现了很多限制!这个不能碰、那里不能去、别坐那边。政府拼了命似的执法——这是为了保护你们,确保他人的生存。”
曾经因为工作劳碌每天都奢望能拥有多一些休息时间的莫谢里夫如今却夜不能寝,夜深人静时就会被恐慌侵蚀。
“你可能会想到工作和金钱,也可能不会。每天我都战战兢兢地测量体温,查了又查。我一边请求神的饶恕一边尝试入睡。我的身体明明躺在床上却怎样也睡不着。我多么希望此时此刻能与家人团聚!”

莫谢里夫第一次离乡背井来新加坡工作是在2008年。他原本在孟加拉经营着一间书店,但是当地政府突然指他的书店所在的建筑物属于非法经营,他只得被迫关店。店里的一名顾客当时指点他不如考虑来新加坡工作。
后来莫谢里夫付了8000新元给当地的一名中介,帮他找到新加坡建筑工地的工作。就这样他离开了新婚怀孕三个月的妻子,漂洋过海来新加坡。
起初,他的日薪只有18新元,他将钱全部存起来汇回家。来新不久后,他晚上就去上课,凭借努力考取了安全监督员执照。2012年,他在工地找到安全监督员的工作,日薪终于增至60新元。
去年12月他突然被辞退只得回返孟加拉。在那之后,全球疫情在各地区暴发,新加坡也出现确诊,然而莫谢里夫并没像其他客工一样选择在家与家人待在一起,反而决定再次启航,3月回返新加坡。
他的目标很简单,希望这次能够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改善家人的生活。不过幸运女神似乎失约了。在疫情和阻断措施的影响下,这一切变得更困难。后来他居住的宿舍变成了感染群,一夜间所有的客工都被隔离。
宿舍成为感染群在意料之中
隔离期间的日常生活很普通也很单调,关注新加坡每日新增病例是莫谢里夫的日常活动之一,染病客工的数字天天都以惊人速度激增。
对正在与七个人共住一间房的莫谢里夫来说,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毕竟客工们的生活空间确实就是那么紧密又狭小。再加上他们每日出勤的交通工具就是那无比拥挤的罗厘,要避免肢体接触根本是痴人说梦话。
对此,莫谢里夫提出了微薄的请求:
“(新加坡)政府应该在疫情过去后,重新思考这些(住宿条件)问题。”

手停口停忧心如焚
隔离第一天,莫谢里夫的耳朵对于突如其来的寂静感到很不适应。
“以往,这个时间大家都赶着去上班。冲凉房外会大排长龙,准备好后罗厘就会来载我们。今天,什么动静都没有,连一根针掉落都能听得清。所有人都醒着,他们的眼睛是空洞的。眼睛后方,躺着一种前途茫茫的张力。如果我们一直这样无法开工,一个月接着一个月,那些财务问题该怎么办?”
莫谢里夫解释说,客工们多来自各自国家的中产阶级,大家的生活就是一道加减乘除的数学题。孟加拉和印度的客工们如果停止往家里汇钱,将会是灾难性的结果,肯定债台高筑。因为许多客工都是借钱举债才得以出国工作。
一旦一个月的钱没定时寄回去,偿还债务的计算法将被打乱,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那种痛苦只有客工们才能感同身受。
“平日里不念经拜神的,现在都在宿舍的公共区域祷告,他们当中有些人从来都没拜过神。死亡的恐惧笼罩着大家,加上各自国内的疫情也很严峻,再坚强的人都坚强不起来了。”
“客工们经常用免费的Wi-Fi给家人打电话,视讯会议时很多都情绪激动大声说话。我每天都会看到孩子们紧绷的脸。我多么希望我能将他们拥入怀里亲吻他们的额头。啊,多久没听他们抱着我手臂喊我Baba了!”
莫谢里夫也介绍说,他的7名室友来自孟加拉、印度和中国。大家年龄差距很大,各自都有烦恼。
“那名中国客工62岁。虽然他的两名孩子都已成年,也不跟家人住,他每个月还是汇钱给他们。他也将薪金的很大部分花来买酒和上赌场。如果我问他问题,他会盯着我看,像一名孩子一样。没有梦想的他,不知道应该拿生活怎么办。”
莫谢里夫不清楚公司会否给他们提供经济上的支援或是稍微补偿他们。他只知道很多客工至今还未领到月薪,囊中羞涩的他们只能省吃俭用,吃着免费供给他们的油腻腻伙食。
“有些印度年轻客工傍晚就喝酒然后躺在地上,他们的生命似乎在龙卷风中滚动。”

和全世界的人一样,莫谢里夫相信疫情总有结束的一天,大自然也会重新接纳人类,在那之后他还是可以继续工作。
尽管如此,现在的他每天睡醒时总会泛着一个念头:
“我想回家。”
对莫谢里夫来说,在这关键时期,环境安全和回家团聚都是奢侈的念头,只能想不敢奢望。
此时此刻,不知道本地有多少民众正在埋怨着微不足道的禁足不便,正为着与家人只能安全地待在家中觉得好闷,为这样奢侈的念头而烦恼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