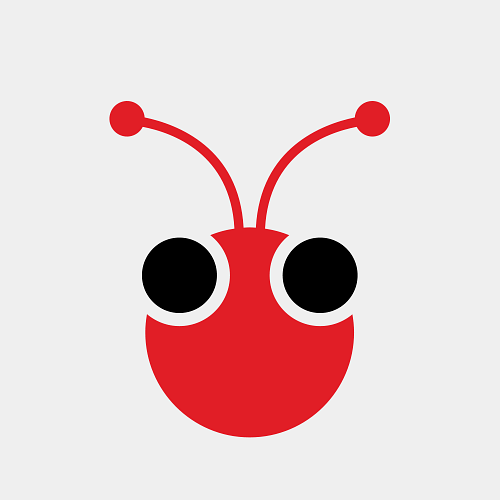‘O’水准会考的成绩在1月12日放榜后,两万多名学子也随之面临求学生涯的重要抉择:
选择到初级学院,还是理工学院升学?
要在初院和工院之间做抉择,除了可供选修的科目和学生个人的喜好,其实还包括了家长对子女的期望,甚至国家社会对学生的期待。
本地两家英文媒体配合’O’水准会考成绩放榜,各刊登了一篇评论,探讨两位作者当年收到‘O’水准成绩之后,如何踏上与多数同学不一样的道路,找到自己的一片天。
两位作者分别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和在籍大学生,正好反映了两代’O’水准毕业生升学的心路历程。
投稿《海峡时报》的June Yong回忆起大约20年前决定报读理工学院,而不是初级学院时,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况:
“(为了报读工院,)我得跟父母认真谈判。当时,连我的同学都认为我疯了。我就读的中学里,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看法,认为一些学府比其他的优越。最终,我的同学大多数都考进顶尖初院。
但我父母最终还是退让了。结果,我的中学有三名本可升上初院的学生报读了工院,我就是其中一人。”

June Yong观察到,’O‘水准毕业生在20年后的今天拥有更多选择: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出国深造,不愿意升上初院或工院的学生还可以报考国际文凭(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再者,本地的教育制度与时并进,不再像过去一样那么重视考试成绩。
June Yong因此建议家长不要将自己的期望强加在孩子的身上,而是扮演类似咨询师的角色,引导孩子考虑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志向等因素,再做出决定。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学生Friedel Wong在写给亚洲新闻台的评论里则写道:
“我清楚记得自己念中学时,决定选修文科而不是理科的那种忐忑。大家都认为,念文科可能会限制自己未来的出路。
这种忐忑反映了以“务实”的态度,选择能让自己达到更高专业地位的科目,在新加坡其实还挺重要的......但是这种思维可能让学生为了跟随大众而忽略自己的长处。
由于我按照自己的所长选择科目,不仅在初院取得较好的表现,还借此发现自己对行为科学的热爱,因而得以升上大学,主修社会学。”
Friedel目前是大三学生,因此估计她是大约5年前参加’O’水准会考,和June隔了大约15年左右。
从两人的经历看出,相隔15年,人们对中学后到哪里升学的看法,比起原先的“大学至上”开阔了许多,至少要跟随自身意愿选择升学途径的学生,已经不再被人视为“疯了”,仅仅只是克服内心的“忐忑”就已足够。
跟人们这种心态上的转变平行的,除了社会对成功的定义,还有我国经济对人才的需求。
新加坡独立后的前20年左右,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当时人们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大学生还只是少数。
进入90年代,新加坡已转型成资本密集型经济,对工程师的需求激增。
当时还在念中学的红蚂蚁就记得老师谆谆叮咛,要念好理科科目,将来上大学念工程系,毕业后当工程师服务社会。
同时,随着经济繁荣,大家都向往更高的生活水平,家长因此更倾向让孩子到大学深造,以一纸文凭保障未来。上面提到的June Yong相信也属于这一代。

到了本世纪初,我国经济转型为知识型经济,近年来科技更是日新月异,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这个年代的人才除了大专教育所提供的专门知识,更需要不断吸收新知识的能力。
同时,我国政治领袖相继呼吁国人重新审视对成功的定义,减少对大学文凭的重视,教育界相继出现艺术学院、体育学校等学府,大专学府纷纷增加学生可选修的学科,让Friedel Wong这样的学生可以按自己的所长做选择,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发挥才能。
我国教育制度和政策,以及社会对学术成绩的重视,就这样沿着国家的发展轨迹演变。
已故企业家沈望傅曾在其著作《千禧年后的狂想曲》(Chaotic Thoughts From the Old Millenium)中,质疑新加坡人长期循规蹈矩,是否真的有能力创新。
June Yong在总结时也提醒读者:
人生是一条迂回的路,一个人最终的成就更可能取决于自己有多愿意向他人学习,而不是学历。
“乖乖”地配合国家的需要,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开创新局面,虽然是看似矛盾,但新加坡人要在未来立足,恰恰就得实现这个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