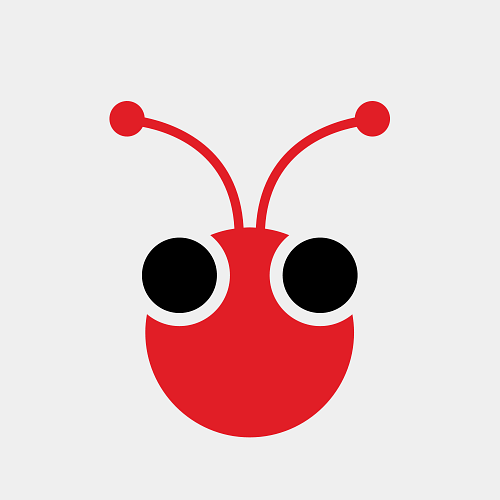上个月,《凤凰周刊》微信号上发表的文章“第一批免签去新加坡的中产,已经破产了”,引起不少人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提到游客在新加坡“特别容易被罚款”。
“特别容易”虽值得商榷,但新加坡很多方面利用罚款预防公众违法,确是实情。
从在吸烟区以外抽烟,到用餐后没有归还托盘,都可能面对罚款;国家环境局日前公布的数据也显示,当局2022年针对乱丢垃圾行为开出的罚单,同比前一年增加了约四成。
去年也有人在网上议论,本地醉酒驾车案例不断增加,跟刑罚太轻有没有关联。
增加罚款固然能起到更大的阻吓作用,但是该增加多少、针对谁加重刑罚?一名《海峡时报》读者日前提出这样的建议:
罚款若按违法者的收入而定,不将现行罚款金额放在眼里的高收入者要罚得重些!
芬兰百万富翁超速被罚17万新元

该读者建议,当局可以考虑效仿芬兰的法规,按违法司机的收入制定超速或闯红灯的罚款金额。
他还毫不留情地指出:
这才会使一些有钱又鲁莽、却又不把当前罚款金额放在眼里的的司机感觉到“肉痛”。
这位读者也根据自己在荷兰和德国生活六年的经验,建议新加坡当局参考外国执法单位的做法,如在高速公路上安装更多闭路电视,并将它们连接至人工智能系统,记录违规驾驶者的行为,并立即开出罚单。

这种“按收入罚款”的概念在亚洲国家没有先例,但在欧洲国家却相当普遍。
芬兰就实施“按日罚金”(day fine)制度,即根据肇事者每日的平均可支配收入来计算罚款金额。
以超速为例,当局会根据司机超速的严重程度,判他罚款多少天的每日罚金,最少一天,最多为120天。
据欧洲新闻台报道,芬兰的每日罚金最低是六欧元,但没有上限。
去年,芬兰一名商人安德斯·维克洛夫就因超速,被罚款12万1000欧元(约17万6230新元),还被吊销驾照10天。
当地媒体报道,维克洛夫是一家年均营业额达3.5亿欧元(约5.1亿新元)的控股公司的董事长兼创始人。他过去10年内也曾因超速两度被罚款,罚金共达15万8680欧元(约22万8500新元)。
他当时接受媒体访问时说:
“我真的很后悔……(事发时)我已经开始减速,但可能当下反应不够快。”
芬兰其他轻微罪行的罚款(例如偷窃),也遵循同样“赚得越多就被罚得越多”的道理。
除了芬兰,瑞士及其他北欧国家也实行相同法规。
在瑞士,曾有一名司机因以290公里的时速驾驶被捕,结果被判处110万瑞士法郎(约166万新元)的罚款,相当于每天需缴付3600瑞士法郎(约5430新元),破了当地的罚款金额纪录。
“差别化罚款”惩罚的究竟是什么?

这个罚款制背后的原理其实与税收相同,个人收入越高,缴付的所得税自然也更高。
但一个是缴税、一个是罚款,履行公民职责和为过错付出代价,不一定能相提并论。
大家心里的第一道问题想必是:视收入而定的罚款制,惩罚的到底是什么?
一名《海峡时报》读者投函讨论这个课题时,以超速为例,说明1000新元的罚款可能会显著影响一些人的收入,但对月入在六位数或以上的高收入者却不足以起到阻吓作用。
该读者进一步举例说,新加坡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实施“差别化罚款”(differentiated fines),比如在个人资料保护法令(PDPA)下,最高罚款金额为100万新元或违法企业年营业额的10%(前提是该企业的年营业额超过1000万新元),视何者为高。
认同这个机制的人所持的立场显然是:同一笔罚款金额,在收入较高的违法者看来“不痛不痒”,因此他们缴付的罚款应与收入较低者有别。

法律之下人人不再平等?
《海峡时报》还刊登了另一名读者的文章,标题就直接表达反对立场:“根据收入制定罚款,让法律显得荒谬”。
这名读者指出,如果一定要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在罪犯的监禁期限。
“一名高收入者判监一个月可能会损失超过一万元,但只赚取最低收入者若判监一个月,可能只会损失几百元的收入。那么,后者是不是应该入狱更久,受到的惩罚才跟富裕人士对等?”
该读者最后说,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罚款也有确切的金额,因为违法者收入较高而给他判处更重的罚款,意味着他受惩罚的原因不是违法,而是因为赚得比较多。

除了上面三封来函的论点,同样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按照收入罚款即使能让收入较高的违法者感到后悔,会不会有反效果?
例如,收入较低会不会成为被告求情的理由,罚款较轻会不会诱使他们以身试法?
高收入者会不会像第三名读者所提到的那样,认为自己是因为赚得太多才被罚,而无法信服司法制度?
要确保罚款公平,还要有足够的阻吓力,除了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人们能否接受罚款与个人收入挂钩,也是司法部门必须考虑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