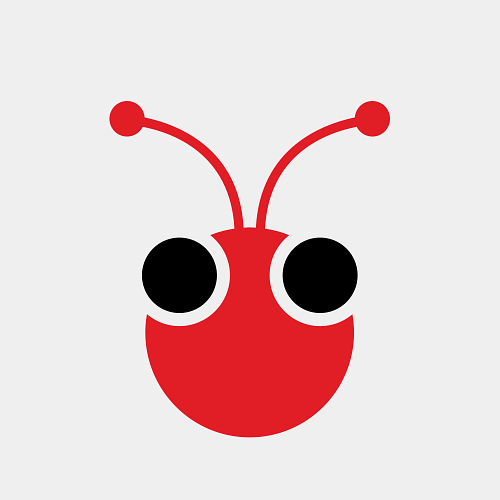上世纪1990年代,红蚂蚁念小学的时候,一放学就迫不及待跑到学校附近或住家楼下的“妈妈店”,买零食和冰淇淋“犒赏”自己。
令红蚂蚁意外的是,现在的小学生竟然也会这么做!
在顺福路第304座组屋经营“华利”妈妈店的Kelvin Lim告诉《海峡时报》,如今小学生已成为他的主要顾客群。
小学生的父母呢?不是去超市或购物商场,就是网购后等货送上门。
也难怪他会感叹,再过几年可能就要关门大吉了。

全新加坡仅剩240间“妈妈店”
建屋发展局数据显示:
这些俗称“妈妈店”(mamak shop)的邻里杂货店已从1980年代“全盛时期”的560间,减至目前的240间。
这里的“妈妈”,指的不是上门光顾的家庭主妇,也不是经营店铺的老板娘。
“Mamak”在淡米尔语是“大叔”的意思,所以准确来说应该叫:印度大叔杂货店。
(还是叫“妈妈店”比较顺口,对吧?)
早期的“妈妈店”多数由印度同胞经营,但他们可都是语言天才!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甚至是福建话和潮州话等方言,都难不倒他们。

几平方米的小空间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零食、酱油、药品、肥皂、电池、卫生纸、文具、玩具、杂志和漫画……
店外的冰箱还有汽水、果汁和冰淇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有趣的是,货品的摆设似乎有它自成一格的分类逻辑。要什么就说一声,印度大叔会像小叮当那样从百宝袋拿出来给你。
没带够钱?没关系,先拿去用,下次再还。
每天早晨不到7点就开店,直到晚上10点才打烊,“妈妈店”一年365天风雨不改地为居民送上温暖。
“妈妈店”月租1500元 相当于一星期的营业额
不过,小型杂货店的货源,毕竟不像大型超市那么多样化。
随着组屋周围的超市和购物商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首当其冲的就是“妈妈店”了。
68岁的詹娜敦(Jannathun Abdul Hamid)在淡滨尼41街第425座组屋经营“妈妈店”已有30多年。
她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时说,首20年的生意一直很稳定,但自从附近开了一家超市后,“妈妈店”的营业额猛跌了超过50%。
“超市那么近,走路十分钟就到了,而且卖的东西也比我们多,居民不再那么依赖‘妈妈店’了。”

更令她担心的是,店铺的月租逐年上涨,如今已升至1500新元;但营业额却每况愈下,从十年前的每日1000新元,跌至目前的200到300新元。
在顺福路经营“妈妈店”的Kelvin Lim也面对同样的经济压力。
自从附近的汤申——东海岸地铁线启用后,人们不再需要穿过顺福路组屋区,就可通往汤申路上段。
随着人流量减少,“妈妈店”的生意也下跌了两到三成。
就连报贩每日送来的报纸,也从之前的20份减至目前的五份。
“以前还会有熟客天天来买报纸,顺便买饮料和零食充饥解渴。”
“现在大家看新闻也上网,买东西也上网,地铁站附近又有那么多便利商店,我们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身为第二代店主的Kelvin Lim坦言,当初是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且行动不便,才会辞去科技业的工作,接管“妈妈店”的生意。

这些年来,他也尝试为老店转型,包括采用PayNow等无现金付款方式,以及为居民提供Shopee电商平台的取货服务。
但50多岁的他仍感到力不从心。
Kelvin Lim解释,店里任何时候都有100到200个包裹等待领取,遇到电商平台推出特别促销活动时,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我自己一个人翻找包裹,非常耗时,还得同时应付来买东西的顾客,人龙越排越长。”
“我真的累了。”
不过,“妈妈店”的生意日渐式微,也不完全是店主的错。
学者指出,不断变化的组屋设计也“难辞其咎”。
新加坡——瑞士苏黎世联邦科技大学(ETH)研究中心的“未来城市实验室”主任施勒尔德(Thomas Schroepfer)教授说,新式组屋的底层空间比旧式组屋小得多,恐怕容纳不下零售店铺。

但他强调,这些一般由家族经营的小型“妈妈店”,仍有它存在的功能和价值。
“它在社区里备受居民信赖,有助于加强社区凝聚力和‘甘榜精神’,在许多新加坡人的心中也占有特殊地位。”
的确,活在“网购时代”的消费者,当然很难对“妈妈店”的经营模式产生共鸣,更别说是感受当中蕴藏的人情味。
不论网购再怎么方便,红蚂蚁还是希望住家楼下有间“妈妈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