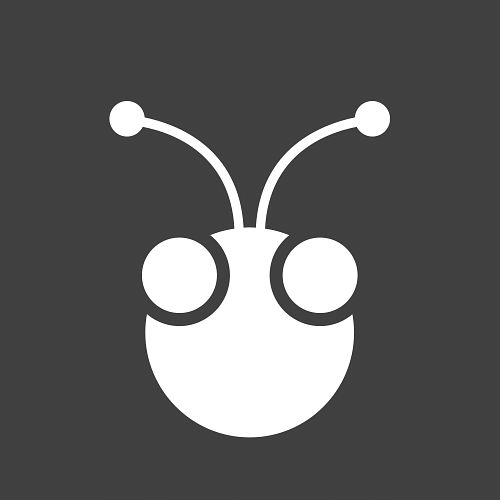每年的12月5日是联合国大会定立的国际志愿者日(International Volunteer Day)。这个在1985年定立的日子,其目的是为了肯定义工的贡献,并鼓励更多人加入义工的行列。
新加坡对于义工和志愿服务的重视,也体现在政府为首推广的各种社会服务项目,如新加坡青年志愿团队和社会自发组织等。

这些项目培养了下一代的志愿服务领袖,同时也把行善事业回归于基层,对社会凝聚力与和谐度都打了一剂强心针。
尽管如此,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每个义工的体验并不像宣传所看到的那样绚丽多彩。过度渲染某些人或组织可能造成毒性正能量(toxic positivity)。例如,把志愿工作中遇到的不公行为正常化并视而不见,就很容易导致志愿服务质量下降。
一个成功帮到对方的案例背后,往往藏着无数个失败和处处碰钉子。
前线的义工若对机构作风心生不满,或者在志愿工作中经历挫败感甚至产生心理创伤后,小则造成义工的流失,大则出现匿名举报和媒体投诉的可能。义工虽然是“免费劳工”,但他们的心理健康同样需要受到关注,也须得到相应的尊重。
社会企业和非营利团体的界线愈加模糊
随着社会企业和非营利团体的界线愈加模糊,我们也看到某些所谓的社企或非营利组织的领袖们衣装光鲜,时而像西装笔挺的生意人,时而又像网红一样通过社交平台经营自己的形象,展现个人魅力来吸引更多义工。
当然,他们很可能单纯只是为了维持专业形象,但在心理学上也可以解读为过度补偿某方面的缺失。这种缺失或许会成为组织风气日后败坏的伏笔之一。
其中一种可能性就是所谓的同理落差(empathy gap),也就是个人和他人的评价产生分歧,导致组织领袖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厌恶上。
这种分歧的根本,其实源于志愿者是免费的劳工。义工往往承担大部分的前线工作,但未必会有得到类似有薪雇员的待遇。
无偿服务不等于可以“呼之则来挥之则去”

为了更好地管理大批义工,听闻有些机构甚至强制志愿者在受训后必须担任义工两年之久,或服务达到特定时间才颁发义工证书。
然而,这也无形中严格管制了义工的自由。这些陋习或者“无意识”的做法,容易构成一种羞辱和压迫的行为,并或多或少影响受益对象的服务质量。
其次,组织中实体义工和虚拟义工之间的不平等待遇也是重要问题之一。
虚拟义工在疫情期间虽然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却因为没有实体义工那样实地现身服务而不免受到冷落。
研究已证实,虚拟义工对组织的归属感和满足感通常比实体义工低。虚拟义工多半都是技术甚至专业性质的。
目前新加坡许多义工的服务内容仍属于不需要技术含量的工作。这本质上对义工来说是好事,因为参与的机会提高了。
然而,对于那些有技术需求的非营利团体而言,它们就不得不聘请专业人士,甚至是引进国外现有的方案来协助运营,但这就需要大笔捐款来维持。长此以往,非但不可持续也不符合经济效益。更何况,有些专业人士和方案还存在文化和语言的差异。
小团体难以得到支援?

令人欣慰的是,新加坡许多年轻人都开始投身自发组织的活动,也提出很多有创意和低成本的项目,而且大致上都可以弥补一些大型非营利团体和公共机构的技术问题。
我們也确实看到了一些通过比赛方式而诞生的社会企业和非营利团体。
然而,我们的社会当中还存在着不少知名度不高或者没有“业绩”可言的小团体。它们在资源上并不宽裕,甚至还会经常被大机构拒于门外,有些甚至面临被解散的命运。
一些大机构甚至会以“只和政府与注册的慈善组织合作”为由,来拒绝与较小的团体合作。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我国鼓励人们从基层自发组织又有何用?这何尝不也是变相歧视的一种?
除了在倡导的内容上有些许不同之外,这些较小的组织通常都与大的非营利组织在争取同样群体的捐助和政府资助。由于它们规模相对小,没有能力提供更高技术的服务而往往难以做大,于是就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总体而言,讽刺的是,这何尝不是一种社会恃强凌弱的缩影?
志愿工作的初衷虽然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但有时候,帮助他人的人与组织反倒成了被欺压或孤立的对象。
国际志愿者日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
我相信志愿工作者都值得表扬,但他们在投入工作前必须先有所觉悟,清楚知道当中所涉及的挑战。
一名义工的心路历程难免有血有泪。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功成名就,而是如何在逆境中失败后,依然保留一份回馈社会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