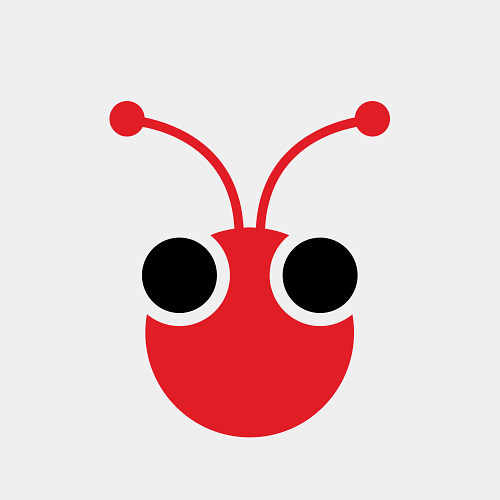在新加坡病了看医生不仅昂贵,还得一等再等,无论是安排检查或治疗都遥遥无期?
《海峡时报》昨天的一篇报道,就活生生地反映了上述情况。
73岁的陈女士(假名)因便秘了好几个星期,即使吃泻药也没效,后来更是出现便血,2021年1月到综合诊疗所看医生。
医生担心她可能罹患结肠癌,让她接受结肠镜检查来加以确定。
陈女士被转介到新加坡中央医院看专科医生。
由于政府医院当时为了应对疫情忙得不可开交,为了确保医院床位充足有能力应付冠病确诊病例增加的突发情况,所有非紧急病患的手术都被推迟了好几次,所有非紧急的医疗程序,包括各种检查,也只能往后排期。
结肠镜检查属于日间手术,将内窥镜插入直肠和大肠,检查息肉和其他癌症迹象。属于“非紧急”范畴的结肠镜检查的预约,于是乎就必须等上五个月,也就是要到去年6月才能进行。

我国卫生部医药服务总监麦锡威副教授在最近的记者会上曾表示,由于要处理积压的非冠病患者手术,政府医院依然面临资源吃紧的问题。
他说,这“反映了我们在过去几个月所欠下的债务”,医院会把重点重新放在治疗这些患者。

由于害怕罹患癌症,陈女士不想等待,于是求助于伊丽莎白诺维娜的肠胃及肝胆专科顾问医生韦俊韬。她在去年2月3日求诊后,一周内就完成了结肠镜检查。
她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她不仅罹患结肠癌,而且病情还相当严重,已经扩散到肝脏。
韦医生建议她带着检查结果回去综合诊疗所,再转介到政府医院接受资助治疗。
他向陈女士保证,其他被他送回政府医院的癌症患者都能得到优先考虑,并在两周内接受治疗。
单身的陈女士只有基本的终身健保计划(MediShield Life),她担心任何延误都可能导致她的癌症进一步扩散。因为她的肝脏那时已经长了一个肿瘤,有5厘米大。
韦医生说,延误五个月的诊断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肿瘤,使治疗更加困难。但他觉得推迟两周的时间进行治疗,不会有太大的实质性影响。
最后,由陈女士一手带大的弟妹们,都同意她立即到私人医院接受治疗。他们与孩子们会凑钱支付医药费。
在韦医生的建议下,陈女士最终选择了安微尼亚山医院较便宜的六人病房,医药费介于5万至6万新元。终身健保计划,本应用于资助治疗,因而只能支付一小部分费用。
陈女士经过几轮缩小肝脏和结肠肿瘤的化疗后,去年6月动了手术,目前情况良好,也没发现癌细胞进一步扩散。
手术后不久,她收到中央医院的信件,通知她说之前预约的结肠镜检查被重新安排到去年11月,再推迟了5个月。
换句话说,陈女士如果坚持一等再等在政府医院看诊的话,距离初次看诊10个月后,才能进行结肠镜检查。
她告诉韦医生:
“幸好我来找你看病,不然我要等那么久才知道罹患癌症,到那时候,癌症很可能都恶化了。”

陈女士的遭遇并不是单一事件。
韦医生透露,在过去两年里,他看到相当多社区病人不得不自己支付大部分费用,到私人医院去接受治疗。
许多人告诉他,他们已由综合诊疗所转介到政府医院的专科诊所,但因为预约要等三个月或更长而只得作罢。
毕竟生病不能一拖再拖,不及时确诊和治疗,或许就会错失治愈的最好时机。
冠病期间更多病患转向私人医院,或会推高保费

原本可以到更便宜的政府医院接受治疗却无法这么做,这肯定会造成骨牌效应。
冠病疫情促使更多患者到私人医院寻求治疗,一方面导致医疗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也推高了索偿额,可能导致医疗保险费上涨。
本地最大的两家私人综合健保计划(Integrated Shield Plan,简称IP)业者——友邦保险新加坡(AIA)和职总英康(NTUC Income)都证实,公司处理的私人医院索偿额在疫情期间有所上涨。
友邦保险2019年至2021年的私人医院索偿占比分别为24%、27%及25%,虽有起有落,但整体而言比疫情前高。职总英康的2019年至2021年的索偿占比则是34%、36%和37%,逐年上扬。
病患可以使用终身健保去支付公共医院C级或B2级病房的住院费用,但公共医院的B1和A级病房或私人医院的住院费用,就必须由IP险负责支付偿还。
我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购买IP险,允许他们到私人医院求医索偿。
友邦新加坡医药总监王英成医生相信私人医疗索偿占比会继续居高,因为人们会觉得政府医院的等候时间非常长,比疫情前更久,所以那些有能力转向私人医疗的人就会这么做。情况若持续,保费将因此上涨。
私人医疗索偿涨幅主要来自没购买附加险病人。
有IP险但没买附加险的公众,首3500元的私人医疗费须先自行承担,之后才由保险公司负责90%的费用。
有附加险的人则可让保险业者承担部分或全部医药费,不过那些自2018年起购买的附加险,不再允许业者支付全额医药费。
王英成医生说,未买附加险的病人在疫情期间明显增加。前年初到去年第三季,这批人的索偿就增加了50%。
不过,也并非所有人都这么做。
一部分有购买最贵级别IP险的病人,因为治疗涉及不受保的长期复诊,而政府医院复诊较便宜,所以并未转到私人医院。也有一批人因没有附加险,为减少个人支付而留在政府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