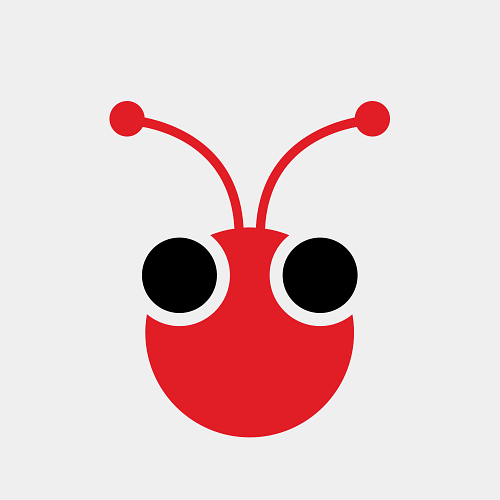视频、文章、微博贴文甚或底下的留言,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内容逃得过无所不在的审查。
近年开始流行,但相对小众的传播媒介——播客(Podcast)可能是唯一的例外。
去年香港反修例抗争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在香港生活的中国播客创作者戚振宇在他其中一集题为“Dear Hong Kong”(亲爱的香港)的节目中,道出了这番与中国主流媒体论调大相径庭的话语:
“我在大陆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关注公共议题的人,但是那时候有很强的一种恐惧感包围着我。当我想去为一件事站出来的时候,心中有好多好多的恐惧……进而因为这种恐惧产生了一种无助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香港最难能可贵的是,当很多人去为公众议题发声的时候,站出来的时候,会有一群人跟你一起站出来……让我知道人生的终极议题就是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会觉得你坚守的一些价值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无谓的……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来收买的,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权力来摆布的。”
戚振宇谈论中国另类生活方式的播客频道《无业游民》是当地极为热门的播客之一,曾获选为中国区苹果2019年度最佳播客。
“大逆不道”的言论为何能逃过审查机制的“法眼”?为何被视为言论自由的最后一片净土?

“用说的,别用写的”
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平均每集播客有20万人次收听率的《博物志》主持人于婉莹,回忆四年前她因为批评杭州政府而被短暂扣留的际遇,那件事让她学会如何钻审查机制的漏洞:
“用说的,别用写的。”
中国网络审查机制拥有先进的技术,但执法人员却往往是对时下潮流一无所知的人。
“他们当时问我是干嘛的,我说我是做播客的,他们反问我,什么是播客?”
正因如此,以音档存在的播客成了一种能侥幸逃过审查机制的传播内容。
如果内容可能触动当局敏感神经,那就“用说的,别用写的”,把审查机构可能盯上的敏感话题用模糊且轻松无害的标题来包装。
如于婉莹所言,“用说的,别用写的”。
“Dear Hong Kong”的文字介绍非常“和谐”,说的是“三个二十出头的内地青年,来到陌生又熟悉的香港,学习着成为一个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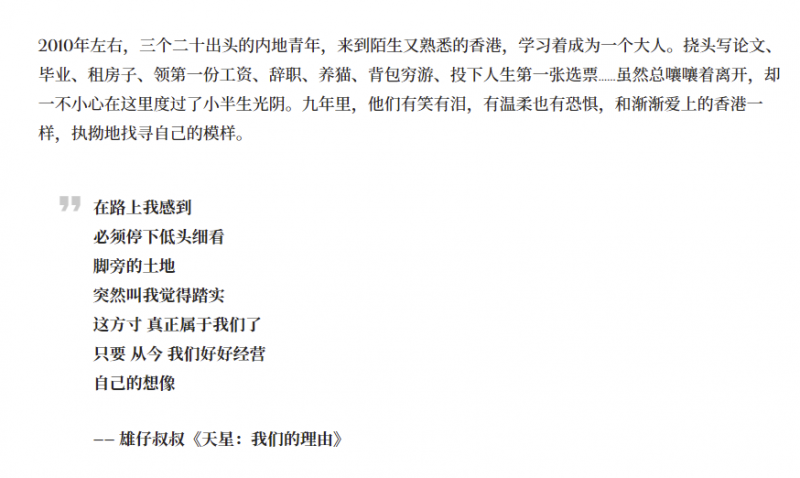
戚振宇解释,该集节目录制当下,香港正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在街头抗争,但直接讨论示威活动无疑会导致播客“被审查”,因此他改而邀请两位大陆朋友一起谈论香港如何形塑他们的人生。
“人们总是说着香港、香港人和香港生活的诸多坏话。但我们的体会不一样。我们可以让他们知道香港正在发生的事,香港没那么不堪,和(中国)媒体所呈现的面貌并不一样。”
他表示,播客可以透过探讨个人经历来突出具争议性的议题。
“我们的感受是真的,我对公共议题的看法也是真的。”
“Dear Hong Kong”就是突破审查框架的最佳例子。

受众增加,自由风气不再
然而,随着受众增加,播客所享有的自由空气日渐稀薄。
根据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国播客产业的年均产值高达30亿美元,商业大户和政府的审查机制开始把触角伸入。
中国播客公司Justpod 联合创始人杨一直言,越多听众意味着更严格的审查。
同时,播客产业越来越商业化,制作人就会渐渐把节目内容往主流课题靠拢。
杨一认为,商业资本的介入,以及进入主流市场势必会引来政府当局更严厉的审查,因此播客平台保有相当言论自由的前景是悲观的。
“如果有人是为了想要自由发表言论才制作播客,那他们现在可以收手了,因为这样的氛围势必会在一年至一年半内开始消散。”

被全面封杀的《剩余价值》
事实上,播客作为突破审查枷锁最后一片净土的日子可能早已成为过去式,像戚振宇和于婉莹那般“瞒天过海”的经历或许只是万里挑一的侥幸而已。
三位女性媒体人发起的泛文化类播客《剩余价值》今年二月就因为一档《瘟疫、语言和具体的人》的节目而被审查当局全面封杀。
该节目当时采访了北京大学历史教授罗新,后者对政府防疫措施,以及国内日渐膨胀的民族主义提出了非常犀利的批评。
访谈原本只以播客的音档形式流传,但很快被人整理成逐字稿并在微信平台散布。
该集随后在国内网站全面下架,不久后甚至连挂在国际平台的作品难以幸免。
该播客主播之一张之琪在微博贴文:
“不是勇敢不勇敢的问题,是对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已经失去了判断的问题;也不是后不后悔,值不值得的问题,是所有人、所有事情都不可能再倒回到一个月前的问题;不是节目要怎么做下去的问题,是人(我自己或者所有人)要怎么继续生活下去的问题。 ”
同一天,《剩余价值》支付宝账号也一并被“清退或禁止续签,不允许签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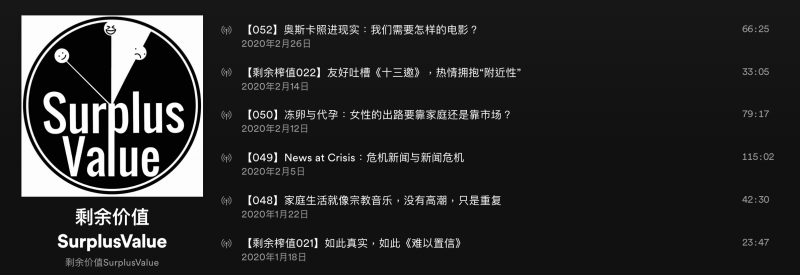
消失的两分多钟
中国播客逃不过三种层次的审查:自我审查、播客平台、赞助人和广告商审查以及政府审查。
戚振宇坦言,他在香港加入新闻业八年以来见证了中国新闻自由的衰落,中国播客面临的困境就是中国新闻自由的写照。
“那时候我们还有希望,还能拥有哪怕一丁点言论自由,以为自己能透过媒体、微博去改变中国。”
“不像今天,所有希望荡然无存。”

如今透过中国网页再点开《无业游民》的那集“Dear Hong Kong”,听众或许会发现戚振宇原来对中国大陆与香港人在公共议题中发表的那番心声早已凭空消失,只有少数网站仍留存着最原始的版本。
不知是当局下令,抑或是自我审查,整段音频长度已从53分31秒缩减为51分21秒,那两分多钟曾短暂冲破枷锁的内容,还是如戚振宇所感叹那般,荡然无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