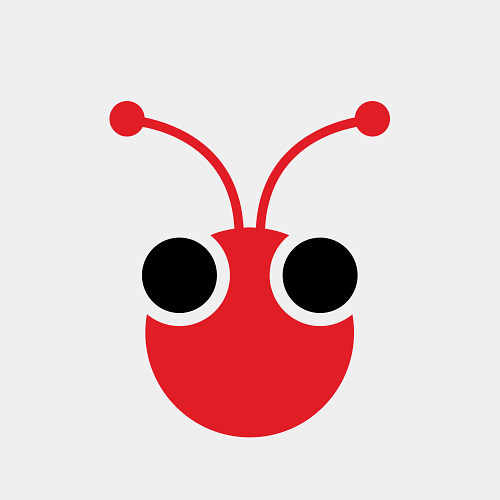新加坡被认为是世界上设计得最好的城市国家之一。不过,策划这小红点的幕后功臣则有两个遗憾。
现年82岁的刘太格曾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市区重建局局长,是我国著名城市规划师,是“花园城市”和“居者有其屋”理念的实践者,他更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不过他本人不太接受这个美誉。
作为新加坡的总规划师,刘太格在建屋局服务了超过20年,提出“卫星镇”规划方案,居民只需5至10分钟就可满足衣食住行需求,避免长距离出行,减少了交通压力。那些年,建设了20多个“卫星镇”,超过50多万个组屋单位,让近八成的新加坡人入住组屋。
刘太格当初按100年的年限、550万人口来规划新加坡的建筑和布局,这个做法在当时被视为非常超前的规划。

日前,刘太格接受美国新闻网站《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采访时回望过去,他认为自己在新加坡的规划上有两个遗憾。
遗憾一:没能为新加坡规划脚踏车道
刘太格说:
“当我在建屋局时,我曾提出为国人规划脚踏车道的想法。当时,我和同事们进行了好几轮讨论,但最终因新加坡的炎热天气决定放弃这个计划,我们觉得新加坡太热了,不适合骑脚踏车。”
他认为,这些年来,新加坡人和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态度已发生了变化。
刘太格说,
(如果可以重来),他希望自己能在道路上开辟脚踏车道,让脚踏车也能安全骑行在街道上。
他说,幸运的是,他相信我们现在还能这么做。
刘太格今年5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提及回首规划新加坡有什么遗憾时,同样提到他应该为新加坡修建脚踏车道。
由此看见,刘太格对没能规划脚踏车道这件事挺在意,也感到非常遗憾。
的确,新加坡的脚踏车道计划落后于很多发展城市,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丹麦的哥本哈根。
新加坡全岛连通的脚踏车道是从2010年后才开始兴建。目前全岛的脚踏车道(cycling paths)总长约525公里,占新加坡9600公里的公路网络(road networks)约5.7%。
陆路交通管理局预计,2030年本地脚踏车道网络将扩增至约1300公里。

新科大建筑学教授施勒尔德(Thomas Schroepfer)告诉《商业内幕》,创建脚踏车道车道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至关重要,既可减少交通拥堵,减少排放,还能通过增加骑脚踏车的活动来改善公众健康。
遗憾二:没能保留任何亚答屋区
最最最让刘太格惋惜至今的,是在规划新加坡的过程,没能妥善保留任何亚答屋区,以致后人没机会亲眼目睹新加坡原汁原味的面貌,从中去见证和感受新加坡在数十年间的快速发展。
因次每每有媒体提出这道“遗憾题”来问他时,他一定会提到这个“痛点”。
上世纪60年代独立初期,新加坡的200万人口中,有将近三分之一居住在环境比较邋遢的亚答屋区和违法兴建的屋子里。
刘太格说,到了1985年,新加坡政府才成功通过建屋局为大约120万贫民提供新的安居之所。

但刘太格说,
“虽然这是一项非常令人满意的成就,但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试图保留几公顷的原始贫民区,让这一代和下一代的新加坡人,见证我国的发展有多迅速。
再多的照片或文字,都无法充分反映贫民窟居民早年的恶劣生活状况。正如我们常说的,眼见为实。虽然今天我们已看不到亚答屋区,但这也反映了新加坡人的生活条件好了许多。”
他早前受访时也说,
如果能留下这样的贫民窟,下一代就会知道上一代的生活情况,可以知道自己有多幸福,一方面感激过去,一方面也减少埋怨。
刘太格想保留类似贫民窟的亚答屋区,新加坡人会有共鸣吗?
新加坡社科大学的副教授Rita Padawangi认为,若要保留贫民区,也必须考虑到如何安顿住在这些老房子里的人,因为只有当这个地方还有人住,保存才变得有意义。
若要保留有人群居住的“贫民区”,就有点类似中国的“城中村”。
众所周知,住在“城中村”的人一般都会想尽快搬离,毕竟城中村以低矮拥挤的违章建筑为主、环境脏乱、人流混杂、治安混乱、基础设施也不足。有点游离于城市管理体制之外,成了都市管理盲区。
Rita认为,与其保护贫民窟,不如保护新加坡硕果仅存的甘榜或村庄。
她解释说,新加坡人怀旧时,仍然会想起本地的这两个地方:新加坡最后一个甘榜——罗弄万国甘榜,和最后一个村庄乌敏岛。
它们仍然存在,不是因为被特地保存下来,而是因为这两个地方至今仍有人居住,这就是它们变得有保留意义的原因。
位于杨厝港路旁的罗弄万国甘榜,是岛国目前仅存的甘榜,只剩下二三十户人家。由于年轻人都不想继续住下去,目前只剩下少数几名年长者居住在那里。

乌敏岛则是新加坡东北海岸外的一个小岛,住着大约38名村民。
配合乌敏岛计划(The Ubin Project)落实10周年,国家发展部长李智陞6月22日宣布小岛下个10年的发展规划,就包括“甘榜屋修复计划”(Kampung House Restoration Programme)。
乌敏岛计划涵盖五个方面,即保护生物多样性、教育和研究、永续设计和做法、自然休闲,以及社区、文化和历史。
不过,行内人都认为“乌敏岛计划”的启动来得太迟,因为早期没有系统的遗产保留计划,已无法追回这部分失去的历史,甘榜屋其实只是昔日乌敏岛民居旧貌的一小部分。
除了这两个地点,新加坡也有一个最后的渔村——实里达渔村,不知道它日后的命运会怎样?
其实,对于新加坡人来说,城市规划中徒留的遗憾何止这些?
新加坡人深感遗憾的还有:一些具有设计价值和历史价值的老建筑没能被保留下来。例如:国家图书馆、国家剧场、旧国家体育馆、第一个水族館、丹戎巴葛火车站的月台等等。
另外,天福宫的旧名匾已不知所终、粤海清庙的庭园变小、最早的华校之一的萃英书院(创立于1854年)目前也只剩下正门的一面墙。
可幸的是,这几年新加坡开始系统化地保留一些带有集体回忆的老建筑,如黄金大厦和珍珠坊。就不知这种保留外貌但内部焕然一新的保存方式,对于新加坡的下一代有没有具体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