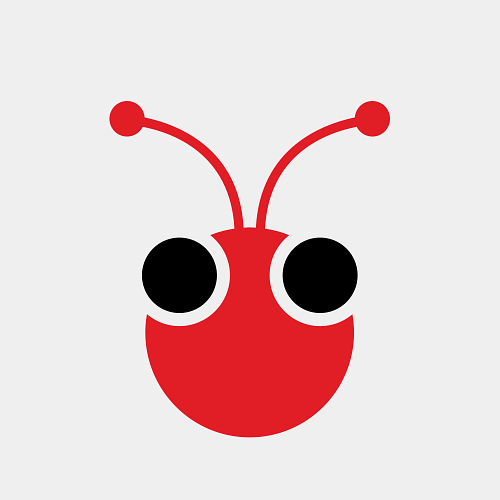红蚂蚁之前打冠病疫苗时,曾见过一个彪形大汉像小男孩般紧闭双眼,针都还没刺到皮肤就吓得鬼吼鬼叫。
其实红蚂蚁自己也是胆小鬼,没资格笑别人。每当有蟑螂飞进家里,红蚂蚁就会放声尖叫,到处乱窜。
朋友却可以很淡定地用拖鞋拍死“小强”,徒手捡起扔掉,然后大笑:
“你那么大只,它那么小只,到底在怕什么?”
是啊,有什么好怕的,红蚂蚁也说不上来。
可能是因为蟑螂的生命力和繁殖力太强,怎么打也打不死?或是因为它又脏又丑,身体油腻腻的,还有一对长长的触角?

有趣的是,“蟑螂恐惧症”的英文学名有够长的,叫Katsaridaphobia。
(顺道一提,“蚂蚁恐惧症”叫Myrmecophobia,蚁粉应该没有吧?)
害怕和恐惧是有区别的
人类在面临危险时感到害怕是正常的。
鹰阁医疗中心精神专科医生林汶龙接受亚洲新闻台访问时说,害怕是一种防御机制,使我们在受威胁时远离伤害,保障自己的安全和生存。
恐惧症(phobia)就不同了,它是一种焦虑症,使人们对某个事物产生非理性的极度恐惧。
患者会竭尽所能地逃避那个事物,一旦接触到就会反应过激,想要逃离,甚至影响到日常生活。
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在100种最常见的恐惧症中,近3%的全球人口患有至少一种恐惧症。
什么东西会让蚁粉心跳加速,直冒冷汗呢?
别跟红蚂蚁说是爱情……
看到别人怕 所以我也怕
当一个人在拥挤的地方经历过濒死的情况,他可能会对人多的地方产生恐惧。
当小孩看到大人害怕猫狗,他们也可能误以为猫狗是危险的,而心生恐惧。
这种恐惧症称为“特定型恐惧症”。怕血、怕黑、怕高、怕打针都属于这个类别。

终身患有特定型恐惧症的人当中,约六成也患有其他精神疾病,例如抑郁症、强迫症或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
林汶龙指出,恐惧症可能由多种因素造成,包括:
大脑强烈的自动反应、过去的创伤造成的条件反射、思维错误、基因遗传和文化影响。
林汶龙曾遇过患有寒冷恐惧症(Frigophobia)的患者。他们极度害怕变得寒冷,不论户外气温有多高,都会用厚重的衣物和棉被把自己包裹起来。
他认为,这可能是文化背景所致。老一辈相信人有阴阳体质,会害怕因为寒冷而失去“阳气”。
心理卫生学院资深临床心理学家刘凯玲遇过最特殊的个案则是患上——华文恐惧症。
“如果小孩对华文产生恐惧,就得把治疗过程分为好几个‘小任务’,例如听我讲华语或念华文故事书,主要是让整个过程变得好玩。”
还好红蚂蚁和蚁粉都没有华文恐惧症,不然这篇文章就没人写、没人看了。
“社恐”不只是内向
在新加坡最常见的还有另一种恐惧症——社交恐惧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简称SAD)。
(嗯,得这个病真的很sad。)
这里指的不是一般的害羞或尴尬,而是害怕面对人群,对外在世界有强烈的不安和排斥感。
患者会因为担心被众人关注或批评,而避免参加小组讨论或进行演示汇报。

还有一种类型是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即害怕封闭或“看似毫无生路”的空间。
新加坡中央医院精神科高级顾问医生林英尊副教授观察到,这种恐惧症在冠病疫情期间尤其普遍。
患者因害怕受感染,而畏惧待在公共场所或在公交上近距离接触他人。要他们接受检测或治疗,也有一定的挑战性。
“疫情把人们减少社交聚会和居家工作等行为合理化。这些患者平时已经依赖‘回避策略’来应对恐惧症,身边的亲友也选择避而不谈,继续回避只会耽误治疗。”
不用吃药也能“康复”
如果不想回避,就要正视和克服!但谈何容易啊。
林汶龙说,治疗往往需要根据个人的具体需求和情况“量身定制”。
心理专家一般会建议“暴露疗法”(exposure therapy),即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下让患者逐步接触他们害怕的事物,降低敏感度,让他们意识到情况其实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举个例子:害怕搭电梯的人,可以先在脑海中想象进入电梯的画面,然后多看电梯的图片,接着慢慢走近电梯,再试着踏入电梯。
适应以上步骤后,就可以尝试搭一层楼的电梯,然后数层楼,“终极目标”是乘坐挤满人的电梯。

如果暴露疗法无效,症状还越来越严重,可能就得服用抑制剂类的药物来控制症状和消除焦虑。
红蚂蚁的蟑螂恐惧症还没严重到需要吃药,但请不要在愚人节拿玩具蟑螂来恶作剧……除非你真的真的真的不想给红蚂蚁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