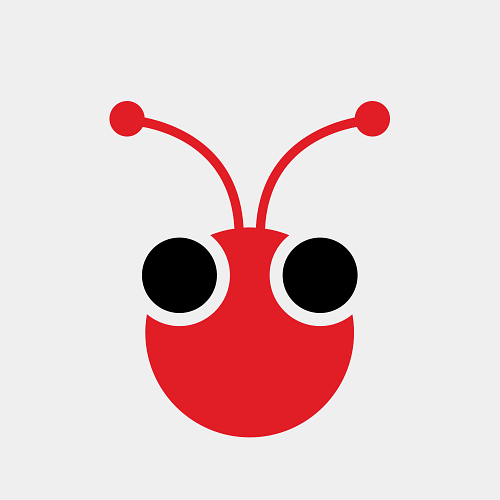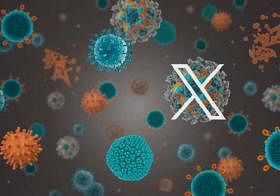
上届2020年大选,人民行动党新候选人的年龄中位数为43岁,较2015年的42.3岁和2011年的38.5岁来得高。
部分原因,是新加坡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新候选人的43岁年龄中位数,也和当年全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42岁相去不远。
但另一部分,也透露出新加坡政党新人难找的困境。
根据一些曾受邀请但拒绝参政人士的说法,政治素人,尤其是年轻人近年来更无意愿跳入政治圈子,大致可归纳成几个因素:
无法蜡烛多头烧;
不想家人受政治攻讦牵连;
社媒时代社会对政治人物过度放大检视。

没办法蜡烛多头烧
据亚洲新闻台报道,一名40多岁,过去几年多次拒绝行动党抛出橄榄枝的私人界专业人士指出,尽管接见选民活动只是一周一次,但议员几乎是每个周末、每个夜晚都有事要忙。
“决定投入政治,就意味着整个家庭都要作出牺牲。”
一名匿名受访的工人党党员(30多岁)也指出,2019年工人党曾邀请她参选,但她拒绝了,原因是不希望占用太多个人和家庭时间。
她注意到,议员往往被期待应该要随时出现在基层。
另一名加入行动党约20年的党员解释,她发现近年来选民对议员深入基层的期望有所增加。
尽管同党义工和其他党员能协助走访基层,让议员无须天天都得到选区走动,但不少选民还是要求见到议员本人,即使团队解释议员有其他要务在身也无济于事。
近年来,年轻世代更注重工作生活平衡。政治工作耗时耗力,吃力不讨好,未必对他们有多大吸引力。
从政也意味着个人无法在职业生涯中继续投注百分百心力。
本地政党普遍上允许当选议员继续从事原本在私人界的工作,但身兼多职,却可能两头不着岸。
对较年轻者而言,从政后政务繁忙,意味着他们得牺牲原本可能的事业发展,
“在政治和基层工作付出的时间,会让你没办法在工作上表现得(与从政前)一样。”
而受反对党招揽的政治新鲜人要承担的风险更甚。
2015年,工人党阿裕尼集选区议员莫哈默费沙接受《雅虎新闻》访问时称,原本在志愿福利团体(VWOs)担任家庭辅导员的他,因“涉入政治而失去工作”。
新加坡国大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等政治分析家也观察到,相较反对党成员,败选的行动党候选人“在能进入和官方有关联组织的情况下”,往往能拥有更稳定和成功的事业。

不希望家人受政治攻讦牵连
几名拒绝朝野政党邀请参选的候选人都不约而同提到,他们不希望家人在政治攻讦中遭牵连。
去年,内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的儿子曾被虚假指控获得莱道路黑白洋房的翻修工程,他被迫亲上火线驳斥传言:
“如果你要对付我,那就冲着我来……但别扯上我的家人。”
从政,一直都不是一个人的事,但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政治人物的家人比过去更容易在政治攻击中被波及。
此外,受邀参政的反对党人士尚有另一层顾虑。
由于本地部分民众仍有着代表反对党出战可能“被对付”的印象,反对党人士的家人更可能因为“不放心”,而不愿意支持他们参选。

当今社会对政治人物过度放大检视
另一方面,随着社交媒体越来越发达,人人皆可评论和抒发己见。
一部视频,几段文字,也许就能引起千层浪。
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过往人生,乃至身边家人,在社媒上几乎无所遁形。
新加坡法律已对政治人物的品格设下高门槛,但选民心中往往还有另一把更严格的尺。
在这种凡走过必留痕迹的氛围下,个人言行一旦出现小瑕疵,都有可能被放大检视,纵使在法律上无疑虑,也未必逃得过网上衮衮诸公的非议。
这种对候选人近乎苛求的检视,让本地政党无从说服潜在新人参政,从事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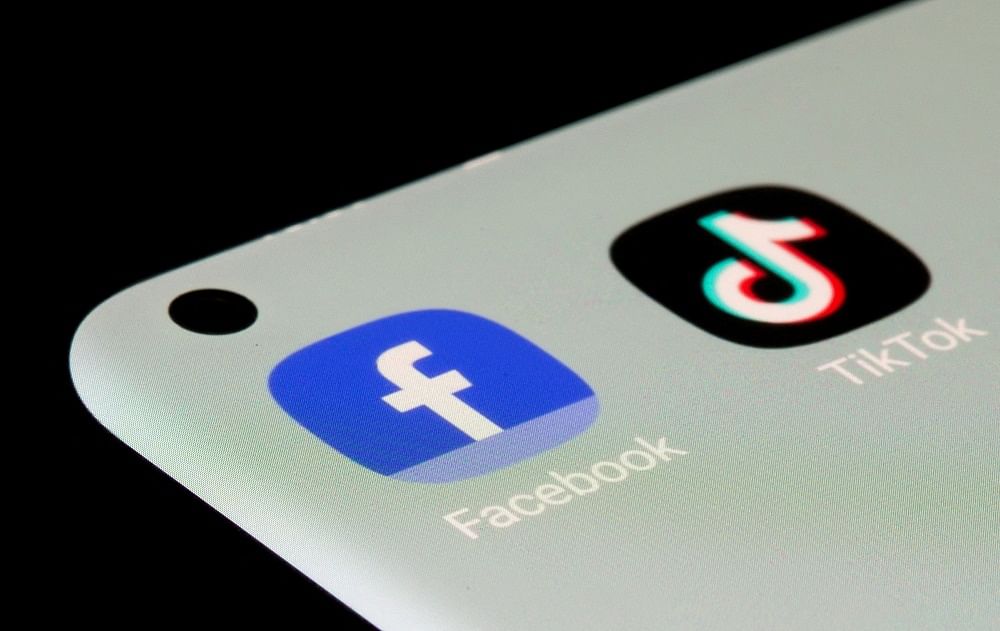
西方国家曾流传过一个段子:
如果有一天要从三位候选人当中选出全球领袖,你会选哪位?
候选人A:曾和腐败政客往来,笃信占星师,有两个情妇,是个老烟枪和酒鬼。
候选人B:有过两次被解雇的记录,常常睡到中午,大学时曾吸食过鸦片,同时也是个酒鬼。
候选人C:是个受勋战争英雄,素食主义者,不抽烟,偶尔小酌,没有任何婚外情。
任何人的首选无疑会是候选人C。
但候选人C其实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而候选人A和B则是带领同盟国阻挡轴心国统治世界的罗斯福和丘吉尔。
对个人道德设下过高门槛,追求所谓的完美候选人,无异于缘木求鱼,反倒让许多有能力有才华的新加坡人裹足不前,不敢参政。
《论语》有云:“学而优则仕”,但在现代社会,出仕显然复杂得多,除了要修身养性,没有一点牺牲奉献精神,恐怕也不敢轻易涉入政治工作。